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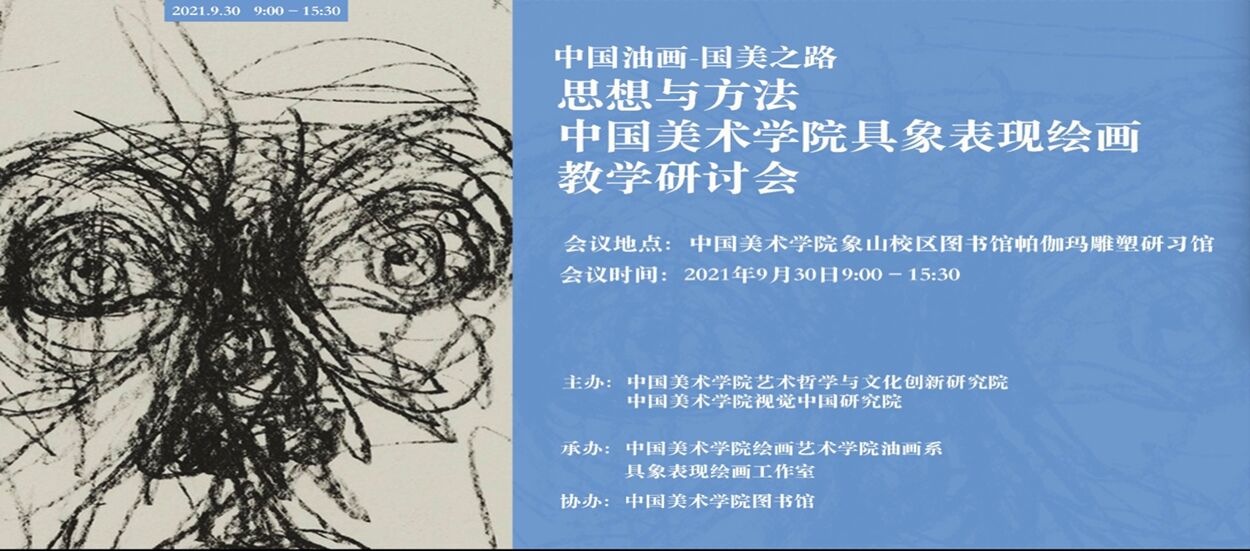



柯律格(中)于2010年

柯律格于1975年摄于北京天坛公园
“我的名片上写着:‘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但我内心里是不是真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史家呢?我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觉得我的有些书更偏向艺术史,另一部分倾向于汉学,我好像在二者之间游移。我所受的训练就是重视文献研究,而不是图像研究。所以,我觉得我思想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斗争。”——柯律格
葛熔金 陆斯嘉
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是研究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前不久,专程来到中国的柯律格就艺术史研究与其学术思想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
柯律格曾任职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长期负责中国艺术品研究及策展工作。近些年来,柯律格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的著述,如《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雅债:文徵明的社会性艺术》、《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等,影响颇大。
2013年,在“牛津艺术史”中文版系列之一的《中国艺术》中,柯律格以前沿的学术观念,盘整解析了中国大艺术史的脉络。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有意取名为“艺术在中国”(Art in China),而不是“中国的艺术”(Chinese Art)。
通过明代自己的声音去了解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很多中国读者对你的了解是从《雅债》开始的,你在书中提到了文徵明与朋友、同乡和同僚之间的艺术品交换和相互支持。
柯律格: 《雅债》不是我关于明代艺术的最早著作,也不是第一本写文徵明的书,更不会是最后一本,因为文徵明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因此我觉得,这部著作不一定要论及关于他的方方面面,不一定要被视为讨论这一主题的空前绝后的唯一著作。
我让读者注意到文徵明艺术和生活的一个方面,这并不代表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内容。我选择文徵明,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拥有与他相关的大量资料。周道振的《文徵明集》对这本书的写作十分重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文徵明本人的文论,这比与他同时期的其他重要人物留下的文字作品多得多,也丰富得多。
艺术评论:你如何理解文人与艺术家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算不算一种赞助?
柯律格: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如果以为两个世界完全相同,那就错了,但如果觉得二者完全不同,这也是错的。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并没有说艺术家不是一个社会性的人。这个观点源自19世纪理想主义哲学,根据这种哲学观念,艺术家没有社会联系。现在,如果我们认为19世纪德国哲学是理解明代的一种合适的出发点的话,我们就应该说文徵明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他是完全独立的。但我不认为康德的理论是理解明代的最佳方式,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明代自己的声音去了解。
所以,我不是在批评文徵明,不是说:“哈哈!原来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19世纪艺术哲学家的思想认为艺术家应该是独立的,一旦他受到任何限制,就是糟糕的事情。但是,明代文献和现代早期的欧洲文献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
遗世独立的天才观念是19世纪艺术哲学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康德等哲学家,而且渗透到艺术史领域,但这并非历史文献的记载。
艺术评论:你如何看其他西方学者使用西方的赞助人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画家的鉴赏活动?
柯律格:让我们想一下16世纪,当时的种种社会各有不同,在那些社会中,图像制作的角色也不同,但也有类似的地方。我觉得你其实是在问关于“西方观看”和“中国观看”的问题,就好像“西方”都是一样的,或者“中国”也是铁板一块。总是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总是关于某种被称为“中国”的东西和另一种被称为“西方”的东西的区别,总是存在一种假设,认为西方与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不同。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假设出发,认为西方和中国彻底不一样,那么我们当然会在证据中发现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寻找绝对差异的立场出发,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些东西很相似,有的内容还真的有点儿不一样,我们会发现非常接近的部分,也会注意到迥然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时代始终还有文人
艺术评论:很多中国读者对你的《雅债》很感兴趣,觉得书中的内容甚至也符合现在的情况,你是否认为《雅债》与今天的艺术相关,不论是西方艺术还是中国艺术?
柯律格:我倾向于认为,一旦作品出版之后,作者就不重要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想法无足轻重。如果读者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那也挺好,我是不是这个意思不重要。我得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当然没想过对当代的情况作任何评价。
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我受到的训练有关,我对自己在英国学术传统中的位置有一种矛盾的感受。我接受了你们所说的汉学训练,然后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我逐渐觉得自己是一位艺术史家。我当然不是学艺术史出身的,所以这个身份总是让我有点儿不自在。我真是“艺术史家”吗?我的名片上写着:“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但我内心里是不是真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史家呢?我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
我觉得我的有些书更偏向艺术史,另一部分倾向于汉学,我好像在二者之间游移。我认为《雅债》的汉学特征要明显一些,因为它基于明代中国的书面文献。我所受的训练就是重视文献研究,而不是图像研究。所以,我觉得我思想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斗争,努力在文本和图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想向世界或者向我自己证明我仍然可以借助明代文献作研究。我觉得这些文献对我来说非常难懂,我经常花好多个小时抱着一本古汉语词典,琢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文徵明的这封信,他的这通题跋是什么意思?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都是对的,很可能有时候是错的。《雅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虽然我成了艺术史家,我仍然可以运用年轻时在汉学训练中学到的方法。如果中国读者觉得这本书与中国当代有关,我认为这很有意思,无论人们在我的哪一本书中找到乐趣,我都会觉得很高兴,但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
艺术评论:“雅债”是一种与文人密切相关的概念,你认为现在还存在这样的文人阶层吗?或者这一阶层已经消失了?
柯律格:有时候我会想写一篇文章,题为“最后的文人”,因为我注意到有不少人被称为“最后的文人”,其中有些人我还见过,比如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先生就被称为“最后的文人”,王世襄先生也一样,这份名单会很长。所以说,文人总是快要消失,但我们的时代始终还有文人。很明显,过去的社会构成与今天不同,“文人”(literati)这个词很有趣,我们说的是“literati”还是“文人”?“literati”其实翻译得不太好,在英语中,“literati”是特指中国的,好像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至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可能过去不是。最早使用“literati”这个词的人是利玛窦,他发明了这个词,他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是个拉丁词,是从古典拉丁文学中来的。它其实不是指“文人”,而是“读书人”的意思,指识字的人。所以我把这次潘天寿讲座第一讲的题目定为“gentelman”,在我看来,“文人”和英语中的“gentelman(绅士)”是一对有意思的概念。你没法要求成为文人,没法填表加入文人阶层,那些说自己想成为文人的人必然不是文人,而说明自己不是绅士的方法就是说“我是绅士”,这样说的人当然不是绅士。这些都是被赋予的社会地位,只要社会还接着这样认为,只要人们认为这些概念还有意义,就会接着使用它们。“文人”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否仍然存在,这不取决于还有没有文人,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还想沿用那个称号。那么,如果今天还有人想用这个称号描绘对象的话,我觉得这个称号仍旧是有意义的。
艺术评论:你在《雅债》里讨论的文徵明和他周围的阶层是属于精英阶层,那在你看来,精英和非精英阶层之间是否相互流通和互动?
柯律格:你们的问题是关于精英和非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资料来源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明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资料来源是不完整的。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你可能知道台北大学的石守谦教授那篇关于文徵明的文章。正如我们所知,文徵明很少画人物画,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山水画,但他也作过人物画,其中之一画的是钟馗。钟馗显然不是精英的兴趣所在,但他也不是一个市井常见人物,他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连结和贯穿。我相信还有很多关于文徵明的资料我们尚未掌握。我们不知道他的宗教信仰,不知道他参与的节日等生活事件。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很有可能参与了特定的节日,而这样的节庆不能被简单地划定为精英或市井的。比如说春节和圣诞节,这些节日既不精英也不市井,就是节日而已。所以我认为有很多领域没有被记录下来,而这些领域正是文徵明日常生活的领域,这部分我们所知甚少。然而有一个英文的表达方式放在这里很贴切: 缺乏证据不是说证据不存在(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中国研究已突破汉学疆域
艺术评论:你从1979年开始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当了十五年馆员和策展人。接触大量馆藏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可以谈谈这段经历吗?例如你个人最喜欢的某些器物。
柯律格:在博物馆里,吸引我的并不是哪一件特定的器物,但我对于在同一时期各种器物之间的联系特别感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明
艺术评论:你能否介绍下英语世界汉学的现状?
柯律格:首先,现在没人用“sinology”(汉学)这个词了,这个词快要灭绝了,人们觉得这个词牵扯的范围太广,包括东方学等等,仿佛是一概而论地说“我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而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已经突破了汉学的疆域,例如,我今早查邮箱,发现收到牛津历史系同仁研讨会的邀请函,但是在20年前,中国历史的教授只会在东方学门类下的研讨会中列席。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外历史研究,会将中国历史也纳入框架内。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扩充,许多没有汉学专业的学校也都开始招纳中国历史专家,例如曼彻斯特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等都开始招聘中国历史老师。正如曹意强教授礼貌地指出,我是艺术史教授,针对中国艺术史工作,而不是中国艺术史教授,这一点很重要。
20甚至40年前当我开始学历史的时候,中国美术史还是在东方学门类下的。40年前有一个机构叫做中国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这个房间就能装下所有成员,大家彼此都认识。现在英国有个趋势,我没法认识所有研究中国的人,因为太多了,研究各个方面的人都有。这是否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教学如何改变传统历史学科教学,而使中国学研究不仅被吸纳在内,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并且能积极地改变学科面貌。而这个问题,人们才刚刚开始思考。当然,最聪明的一帮人已经意识到,一旦我们将中国研究加入到历史、艺术史、哲学、政治研究的整体框架内,那一定不是简单的添加,而是意味着它会对整体思考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在我有生之年也许不会有大改变,但是将来一定会有,这是不可避免的积极的改变。
要研究中国必然需要会中文,我非常不好意思,虽然我能够听懂也能看懂中文,能用中文闲谈,但是我还是很难用中文做一场学术演讲。而英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语言能力的衰退。英语的世界通用使得英国人本来就懒于学习外语,再加上过去20年来政府的政策变化等原因,英国人学习外语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因此为了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就需要聘用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又不能完全了解英语世界。回到《中国艺术》这本书,我很清楚英国人不知道什么,并且如何让他们理解,这又是一些中国学者所缺乏的。在美国,教中国艺术史的老师几乎全是中国人,这是好事,因为母语优势所以学术质量可能会比较好,但是也有负面影响,那就是他们不一定理解西方文化,而无法进行文化转译。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仅熟练掌握双语,而且通晓双文化,如巫鸿。
艺术评论:你曾说过,由于整个大学期间都在与语言搏斗,对理论无暇顾及,直到在博物馆工作时接触到布尔迪厄等理论家的学说,始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中获得启发,利用文史互证的方式进行研究。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在该校出版的《艺术史的批评词类》中负责“艺术社会史”一章的撰述。你是如何深入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的?受到过哪些理论的影响?
柯律格:我认为答案在书本中。我感到微微有些惊讶,中国读者似乎认为我是所谓“理论型”作家。也许在中国艺术的领域确实如此,但是在英国艺术史的领域,我似乎是相对更加传统、更加经验主义(甚至略微有些保守)的学者。
我不认为跨越学科的写作有何神奇之处,如果我认为什么东西有趣,我就会去阅读。我来给你讲讲我1974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的故事吧。当时我的室友是一位中国同学,比我大很多(我当时只有19岁)。当时,出版发行的关于中国过去的学术书籍特别少,我几乎买下了所有看上去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买书有点乱!”他是在批评我,我也这么觉得。我的阅读也同样“乱”,但它会带我领略有趣的地方。关于理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非按照“正确”的顺序去接触它们,并不是按照它们实际产生的顺序。比如,我读硕士时期阅读了爱德华·萨义德的书,之后才接触到福柯。即便萨义德晚于福柯,并且其理论还是从福柯发展而来的,但我当时并不知晓。
艺术评论:你曾经说用所谓的“中国视角”和“西方视角”去解释哪种方法更适合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说法是个伪命题(或者说是错误的)。那么在你看来,从事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
柯律格: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开放性、灵活性,还有勤勉和努力工作。我们拥有大量关于过去的材料,而今它们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研究,我们欢迎任何讲述过去人类的创造性的话题。那比任何固有的观点都要重要,不管是来自哪里的视角。
艺术评论:你认为社会学理论是研究艺术史的工具之一,你极为看重人们的社会关系,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经济因素在社会交往和活动中的分量?经济因素又如何影响了艺术家和广大受众的关系?同时,是否每一件作品的“恩-债”关系背后都有经济方面的衡量呢?
柯律格: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更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比起纯粹的“经济关系”我可能对“权力关系”更感兴趣(这也许是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此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皮耶尔·布尔迪厄的著作,以及他关于不同形式的资本-文化,社会-经济间互动的观点。让我感兴趣的正是这种互动,我当然不认为提问中所提到的“经济因素”更“现实”,更“基本”。在我看来,这种“经济因素”对艺术家的影响的提法本身,就是试图再一次将艺术家置身于人际关系之外,将他们视为经济的被动接受者,而我却将他们视为参与者。
艺术评论:你对理论充满自觉,注重材料和理论间的呼应关系,请问,你如何看待那些以考证事实、发掘新事实为旨归的研究?是否会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的事实研究仅仅是完整研究中的第一步?
柯律格: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基础的错误,也就是假定了存在那么一种“没有理论依据的事实研究”。如果历史教会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在任何的学科领域中,决定是什么组成了“事实”这个决定本身就涵盖了很多理论问题。以艺术家的生活事实为例,为什么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些事实,而不知道另一些呢?其实这就是受了过去一系列意识形态优先选择的结果,事实上我看来几乎就是意识形态的定义。当然,我相信经验事实是存在的,我也希望在我的著书中有足够的所谓“考证事实”,不过我也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又怎样呢?”既然这些事实早已被历史学家所发现,我们再罗列意义何在?
艺术评论:你说自己极其尊重艺术实践,但这对你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你甚至说自己根本没有视觉艺术方面的天赋,并为此感到遗憾。你觉得,“没有艺术天赋”对你的艺术史研究有什么影响?
柯律格:请不要认为我真的躺在床上夜不能寐地担心自己缺乏艺术才华。艺术史对我来说是一种历史的探寻,艺术史学家并不需要是一名艺术家,就像政治史学家并不需要是政治家。也许我知道一些实践者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技巧掌握者可能会误认为自己理解过去的人如何运用技巧。也许缺乏技巧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我可以自由地跨越不同的研究范围,从绘画到家具,因为我没有被任何一种形式所束缚。我们都需要尊重他人的技巧与才华,我也尊重艺术家的才华,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善用自己的才华,思考我们能做什么,而非我们不能做什么。
《中国艺术》
不为永恒流传而写
艺术评论:“牛津艺术史”中文版系列之一的《中国艺术》这本书,从主旨、框架和对艺术品的描述都和当下出版的中国美术史书籍不太一样,你是如何整体规划这本书的构架的?这本书主要从艺术品的社会功能出发来划分章节,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传达怎样的观念?
柯律格:牛津大学出版社要出版系列多卷本艺术史丛书,其中有中国卷,他们邀请我来负责这部分写作。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卷最少需要两册吧。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苏塞克斯大学工作,而我的同事伊芙琳·威尔士受邀编写意大利卷,从1400年到1500年。意大利是一个欧洲国家,威尔士教授可以用220页的篇幅和120张插图来谈论这个国家在100年间的艺术。我也分到220页和120张插图,却要谈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石器时代到现在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很荒谬,我可以说:“不,这事没人能做,我不做。”但是我说:“好吧,我可以试试。”于是,我开始想我能做什么。
反过来看,这本书不是唯一的英文版中国艺术史。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你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所以问题在于“我能做什么使其不同于其他中国艺术史书”?其他人是怎么做的呢?大部分书都是根据时间断代,商周汉唐宋元明清,并根据断代来解释这个时期的艺术情况,但是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些断代毫无意义。重申一次,我不敢说我的方法是唯一可行的。况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没想到会有中文版。这本书我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给对中国所知甚少的欧洲人写的。如果你在伦敦街头问一个行人:“唐和宋究竟孰先孰后?” 没有人会知道答案。所以对于英语读者,历史断代排序未必是最明显有效的讲述方式。
现在回想,我不认为它完全成功,但值得一试。我不自认完美,但也并不为自己的尝试感到抱歉。如果有机会再编一本,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吗?可能不会。我当时的理想读者是英国读者,而这个方法在当时是个好主意。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这类书籍每过三十年就重新书写一遍,我不愿持续修订这本书,而是衷心希望从今天起二十年内会有一本新的介绍中国艺术史的英文书籍,让人们喜欢读,常常用。我的那本书不是为了永恒流传而写的。
艺术评论:在《中国艺术》一书中你将宫廷艺术和文人画艺术区隔开来谈,是不是有失偏颇?在大部分中国研究者看来,明朝的很多画家是难以用宫廷画家和文人画家来区分的,你如何定义那些介于宫廷画师与文人画家之间的群体呢?在第四章“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中,你把北宋艺术与原理放在这一章,可是北宋当时的很多大家都是宫廷画家,你当初这样规划是出于何种考虑?
柯律格:所有的论证框架都有其弱点,我想这个提问本身就已准确抓住了此书的一个不足。这本书并不完美,我愿意承认它的不足。不过章节的标题并不是排他的定义,它们只是作为参考的框架。在这样的一本书中,由于长度被严格控制,还有很多插图,就没有篇幅容许我像原本打算的那样透彻解释这件事。
艺术评论:在《中国艺术》中,你列举了120件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被认可的经典作品,还有一些“恰好不属于传统而经典的重要艺术品”。你选择的原则是作品可以支撑著作的背景。你可以谈谈其中一些作品和它们对你研究的支持吗?
柯律格:如果选择作品的原则没有在书本中陈述清楚,那是我写作的问题。我仅仅只想选择那些我觉得写起来比较有趣的例子,往往其中一些作品已经有相关的有趣的基础性研究。对于英语读者——这本书首要的阅读对象——来说,如果他们有兴趣,他们可以在阅读了我的介绍之后,去寻找到更多研究中国艺术的英语学者的著作,也许他们没有那么有名,但他们同样做了有趣的研究。我希望这些内容阅读起来有趣,对于那些对中国艺术已经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让他们看到已经熟悉的作品,也能够看到一些从未了解的作品。
(翻译 朱洁树 姜岑,实习生孔玉对本文亦有贡献)